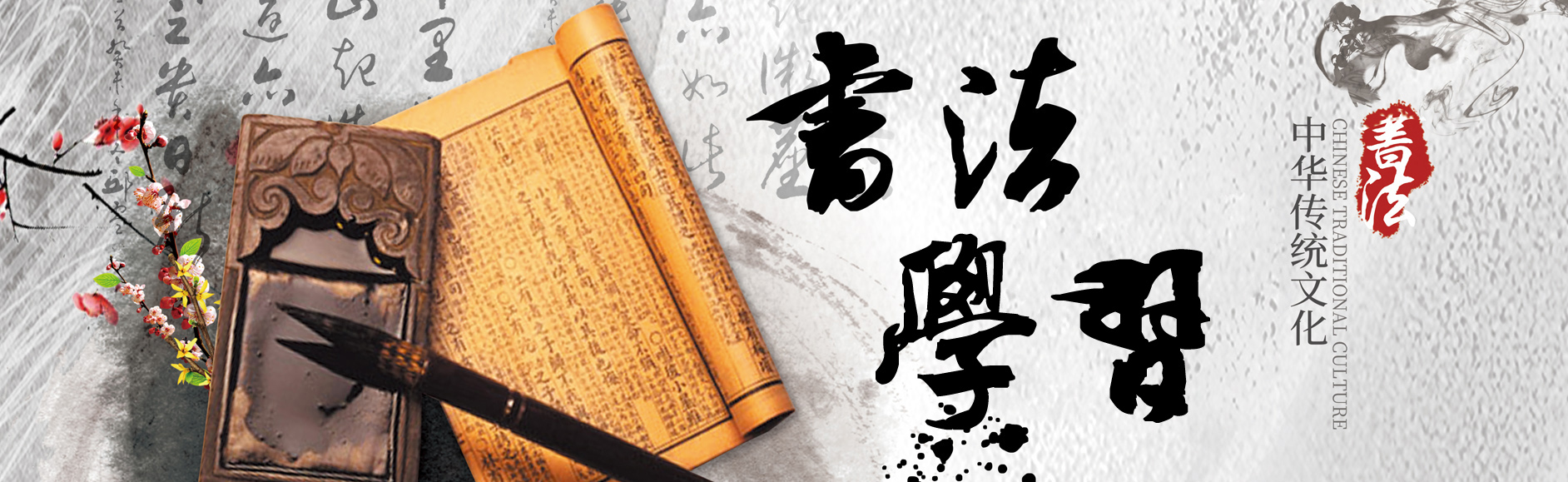现代人由于远离传统,或知之甚少,便以为传统的 山水画千人一面,因循守旧,僵化窒息,不会再有前程的了,于是各种激进、躁动的反传统言论盛极一时,几成时髦。然而,由“上海名片印刷”初涌的昂奋态势稍趋平缓,各类“水墨实验”有所收敛,进而寻求自己的精神 依据时,对传统的再认识,几乎成了不约而同的一种 “回归”。
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山水画,从一开始就是所谓的产物,人与自然的交融、合一,人对自然的崇 敬、热爱和依恋,使画家在对自然进行“描蓽”的同时, 就由于不可避免地掺合着画家彼时彼地的意绪感念而 进人“描写”的状态,假如把“描摹”理解为侧重于对形 的擷取,那么“描写”就包含着精神的抒发了。随着对 自然物、对绘画双重认识的深化,随着某些既符合(或 接近)自然物的表征,又能在人的认识和感知上获得认 同的符号性绘画元素和绘画语言的产生和成熟,传统 山水画便日渐减轻“描摹”的成份而专事“描写”了。这 样,一方面将水墨枯湿浓淡各致其极的无限变化施之 于概念化的符号的排列组合之上,构成某种与人们心 灵相通的情绪化氛围或境界,形成不足与外人道的独 特的审美圈,使绘画在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下,走上远 离众生的象牙尖塔;另一方面,这种“符号”的排列组合 或“符号”本身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呈现出不可遏止的变 化发展的生命力。尤其在元代,披麻玻的变异发展,书 法人于画法使绘画的升华,都足以证明“程式化”只是 向人们提供了一套得以轻松抒发心绪,乃至纵笔进行 墨戏的行之有效的“工具”而已。不难理解,由来源于 形象的“符号”再去构成形象,作者要做的只是水墨的 变化和符号的不同组合,而这两点正是纪录作者情绪 变化,感情宣泄最便捷最舒心的手段。于是,大部分 人,特别是那些文人画作者不思进取,满足于惰性的轻 松的程式而走上僵化的歧途,一小部分人秉于天性,拓 展画理,不断从大自然攫取新的对形象的感受,改变乃 至创造出新的符号,新的程式,形成新的画风画派。末 流或宗师由兹分矣!事实上,堪称宗师的开创性画家尽 管人数不多,却历朝历代都有产生,他们之间由于绘画 观念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不存在可比性,所以很难作 高下的判别,由此也证明了富有开创性的中国画传统 之路并不会就此湮灭。
技进乎道是中国绘画艺术,甚至所有中国艺术的 哲理性共性。技是具体的,程式化的,形而下的,具很 大的可操作性;道是抽象的,纯理念的,形而上的,可意 会而难以言传的,这两个极端在高境界的中国艺术内 部是统一的。技是出发点,道是归宿;技是致美的,道 是审美的。审美涵盖了整个作品的精神气质,致美提 供了不同层次的笔墨轨迹和形象的必然性。
历经数千年递进的传统绘画告诉我们,道与技,审 美和致美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,而致美的“技”又蕴 含着统摄于道的对待形象和笔墨的不同态度。形象可 以是相当明晰的,完备周全的,也可以是恍惚含混的, 似是而非的;笔墨可以是紧扣形象的,由形致神的,也 可以是游离于形象之外,由趣而成形的。图(一)明“ 王绂所作《枯木竹石图〉与北宋绘画相比,笔墨决定形 象的成份就多了一点,如此灵活自由的线条和变化多 端的墨色,说明此画的随意性极强,下笔的出发点就是 笔墨趣味,并由此而构成形象。所以,此画构图并不完 美,枯木与竹石的关系由于取势雷同而显得古板,缺乏 照应,但水墨效果却是极佳的,可谓是由枯湿浓淡各臻 其妙的笔墨趣味来进行造型的一件代表作品。而在宋 代,尤其是北宋,这类山水作品是极为罕见,甚或没有 的。
不管画家对形象,对笔墨取何种态度,也不管由笔 墨决定形象还是由形象决定笔墨,传统绘画总是在画 面上理性地进行着有秩序的,而不是把线 条变成笔触去营造形象。什么是有秩序的平面展开呢?
这幅画中的树法虽已有明显的“蟹爪”、“鹿角”的 分别,但,绝不是文首所述的符号性、程式化的所谓传统 模式的+性表现。这幅产生于北宋中后期的作品构图 奇特,境界幽邃而开阔,点线面与疏密虚实的安排无不 貼妥匀落,且笔法严谨、层次井然,复笔清晰,圆浑整 饬,是一幅从立意到技法都十分成熟和完美的佳作。